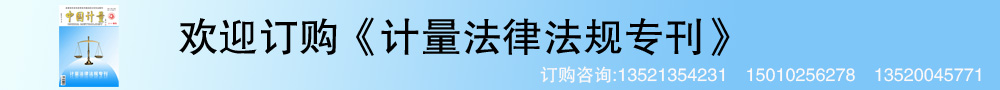
夏商周三代(前2070~前770年),曆時一(yī)千四百多年,是我國奴隸製社會從形成到發展,以至全盛的時期,西周後期,奴隸製逐步(bù)走向崩潰。三代的生產關係主要是奴隸主占有土地和奴隸,實行井田製。社會分工由畜牧業過渡到以農業為主,兼有一定規模的商業、手工業、建築(zhù)業等。由於奴隸製(zhì)發展的需要,度量衡也從萌芽(yá)到產生,開始出現度量衡單位和專用的器具。主要(yào)用於王室和奴隸主上(shàng)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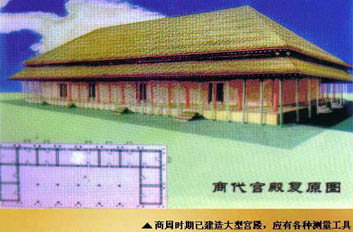
土地(dì)劃分與地積單位
禹不(bú)但治(zhì)理了水患,還“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見(jiàn)《韓非子(zǐ)》)。孔子(zǐ)說:禹“躬稼而有天下”(《論語》),他劃九州,經啟九道。說明夏初中國境內已形成了以華夏民族為中心的(de)大聯合。禹在治水過程中,通過長期實地測量,把居(jū)地分(fèn)為九個(gè)區域。為了便於統治還劃(huá)分了大、小(xiǎo)國的疆界。在土地成為主要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社會,為避免互相爭鬥,定歸屬(shǔ)、劃地界已(yǐ)成為必要。禹把治(zhì)水工程中逐(zhú)步(bù)掌握的(de)大地測量(liàng)技術,用(yòng)於(yú)土地劃分、丈量上。
禹還(hái)善(shàn)於治理農田,他教民耕作,在田間開溝渠(qú),開始了原始的灌溉技術。為了(le)便於耕種(zhǒng)和管理,農田已(yǐ)劃分成規整的方田(tián),並有了固定的單位“甸”。《詩•小(xiǎo)雅》中有:“維禹甸之。”據鄭玄考證(zhèng):“六十四井(jǐng)為甸,甸方(fāng)八裏,居一成中,成方十裏。”由於時代久遠,夏代土地製度的詳情已無(wú)法考證(zhèng)了。僅《左傳》中記載了一(yī)節在禹之後曾發生過一(yī)次奪權鬥爭的故事:少康的父親“相”被寒所殺。少康逃奔世代與夏後氏親善的有虞氏那裏。“虞(yú)思於是妻之(zhī)以(yǐ)二姚,而(ér)邑緒綸,有(yǒu)田一成,眾一旅。”有虞氏(shì)的諸侯虞(yú)思,不但接納了他,還把兩個女兒(二姚(yáo))嫁給他,讓他居(jū)住(zhù)在“綸”這(zhè)個地方,並分配給他(tā)土地一成,眾一旅。“一成(chéng)”是10裏見方的土地,一旅是500人。經過自己的努力和眾人的擁載,終於(yú)奪回了王(wáng)位。後來(lái)史學家稱之為“少康中興”。同時說(shuō)明夏代(dài)土地劃分已(yǐ)有(yǒu)單位和製度了。
井田製的起源很早,但發(fā)展成一套完整的製度,用來作為剝削的手段和俸祿的標準,則是在商(shāng)代完成的(de)。文字是客觀事實的反映,商代有了一塊塊方(fāng)正(zhèng)的田,才會出現那樣四方四正的象形文字。土地是最重要的私有財產,劃分田地必有疆界。甲骨文中有“疆”、“畎”等字。從(cóng)字形上看(kàn)都與“田”有(yǒu)關。《說文》:“畕,比田也。”“畺,界也。從畕,三其界畫(huà)也。”段玉裁注:“信南山,我疆我理。傳(chuán)曰:疆(jiāng),畫疆界(jiè)也。理,分地理也。”“疆”起源於田土之界,後世引申(shēn)為國家郡邑之界。“疆”字從田從弓(gōng)。弓是丈量土(tǔ)地的工具。《儀禮》雲:“侯道五十(shí)弓。”賈公彥疏:“六尺為弓,弓之古製六尺(chǐ),與步相應。”古代還用繩來測量土地。《禮記》雲:“以繩德厚。”鄭(zhèng)玄注:“繩,猶度也。”程(chéng)大位《算法統綜》也說:“古者丈田較闊長,全憑繩尺以牽量。”皆言以(yǐ)繩量(liàng)度。用繩丈(zhàng)量土地(dì)在世界許多古老國家裏也得到(dào)證(zhèng)實。公元前1400年埃及的壁畫上保留著勞作者用結繩丈量土地的生動畫麵。



恩(ēn)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shuō):“數(shù)學是從人的需要中產生的,是從丈量土(tǔ)地、測量容積,從計算時(shí)間和(hé)製造器皿產生的。”數學是數量抽象的科學。甲骨文(wén)中已有十三個記(jì)數單字,最(zuì)大的數是三萬。有了(le)數(shù)字,有了測量單位,有規定了統(tǒng)一(yī)的量值,度(dù)量衡便在一定的範圍內通用了。早在殷(yīn)商時期也確確實實(shí)製造了測量長度的專用工(gōng)具“尺”。
[page_break]
夏商周的(de)賦稅與(yǔ)度量衡
在國家機構(gòu)已經建立的夏代(dài),要(yào)維持(chí)公共利益,就需要公民繳納一定數量的費用——賦稅。《史(shǐ)記》雲:“自虞夏時,賦稅備矣。”賦(fù)稅是國家(jiā)存在的經濟基礎,隨著賦稅的征收,度量衡便成為(wéi)統治者手中權力的象征。
從夏代起,發展中的私有財產製度,逐(zhú)漸改變了原始(shǐ)公社的性質,公社社會在分化,少數人成為生(shēng)產(chǎn)資(zī)料的所有者和統(tǒng)治者,大多數人成(chéng)為自由民,耕種一定數量(liàng)的土地,並向統治者納貢(gòng)。為了(le)均衡負擔,避免爭鬥,必須規定出貢納田賦(fù)的(de)布政(zhèng)施教(jiāo)措施。《尚(shàng)書》中就記載了有關貢(gòng)納的詳細規定(dìng),即將九州的田(tián)地及貢(gòng)賦,劃分成上、中、下三個等級,各種等和級的差別,主要考慮到繳納賦(fù)稅者與帝都距離(lí)的遠近、交通條件、土地肥脊等具體情(qíng)況,分成甸、侯、綏、要、荒五服。後人對《禹貢》的著作年代雖有不同看法,但(dàn)至少可以說明,早在夏商時期(qī),已有各種賦稅製度和(hé)具體實施辦法了。《國語》引《夏(xià)書》中有一(yī)段關於夏代度量衡器的記載:“關石禾鈞,王府則有。”韋昭解:“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shí),今之斛也。言征賦調之鈞,則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guān),衡也。”蔡注曰:“其以鈞石(shí)之役,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也(yě)。”夏代是否已有(yǒu)鈞、石之類度量衡單位尚(shàng)待考(kǎo)證,然而這一則記載可以從一個側麵證(zhèng)明,在建立了國家機構的夏代(dài),專用(yòng)的度量衡器具已是不可缺少的,這些度(dù)量衡器在一定範圍或(huò)一定用途上已具有權威性和(hé)統一性了。在(zài)私有製尚處於萌芽(yá)狀態的夏代,交換隻是為了滿足生存的需要(yào),常常以相互贈送的(de)形式出現,對多少、大小皆不(bú)甚(shèn)計較。而專用的度量衡器往往與繳納賦稅(shuì)有關,一般(bān)都收藏在官(guān)府,由統治(zhì)者(zhě)掌管,成為一種權力的象(xiàng)征,是神(shén)聖不可侵犯的。“關石禾鈞,王府則有”正式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記述。
西周是奴隸社會的鼎盛時期,農業又是當時社會的主要經濟。早在(zài)上古堯(yáo)舜時(shí)期,周氏族的(de)祖先在耕作技(jì)術上就(jiù)頗為擅長。據《公劉篇》記載,公劉在夏後氏政衰之後,被(bèi)迫西遷,流浪到豳地之後,逐漸恢複了周族的農業生產,創造了安定(dìng)的生活條件。為了保障部落的安全,成立了三軍,於是不(bú)得不向各家族征收實物(wù),以(yǐ)為(wéi)軍糧(liáng)。從此,周人的社會生產日益(yì)增長,社(shè)會(huì)分(fèn)工日漸擴大,自公劉起,傳(chuán)了九世,到(dào)了古公亶父(fù)時,這一帶已是人畜興旺,農產豐富的樂土了(le)。但(dàn)是當時(shí)在(zài)涇河流域仍是戎(róng)狄雜居之地(dì),北方強悍的遊牧(mù)民族,對周族聚居的這(zhè)塊土地早已(yǐ)垂涎三尺,不斷(duàn)侵擾。周族不堪外(wài)族侵擾,隻能再次遷徙,來到岐之南的周原,從此自稱周人。他們來到周原之後,首先開拓田疇,劃(huá)分疆場,把(bǎ)土地分配給氏(shì)族(zú)成員(yuán)去耕種。在《周(zhōu)禮》的每篇開頭都有如下五句話:“惟王建國,辨方(fāng)正位(wèi),體國經(jīng)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規定了氏(shì)族總家長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劃分田野為井邑,並設立各級官吏把各部落的人員分別組織到大小邑中。又在王城內興建城郭,營(yíng)造(zào)宮室,逐漸使國家這一體製初具雛形。周人建國之後,繼續發展農業生產。土地作為重(chóng)要(yào)的生產資料受到重視,被(bèi)看成天賜之聖物,周室(shì)的(de)最(zuì)高統治(zhì)者“天子”是土地的唯一所(suǒ)有者,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當然,土地的耕種者還是(shì)廣(guǎng)大奴隸和農奴,為了便於管理,天(tiān)子又必須把除自己管轄之外的土地分封給諸侯,諸侯再以采邑的形式(shì)分賜給大夫,大夫再以一(yī)部分轉賜給家臣。為了適(shì)應分封土地的需要,另(lìng)設專門(mén)的官職(zhí)來丈(zhàng)量。即《禮記(jì)•王製》中說:“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xìng)事(shì)任力。”周代井田製承襲(xí)商代而(ér)有所(suǒ)發展,形成一套計量田土麵(miàn)積的單位製。“田”作為一個計量單位,常常出現在西周金(jīn)文裏(lǐ)。如(rú)孝王時的“曶鼎”記有一則訴訟案:有一年鬧饑荒,匡(kuāng)指使他的農業奴隸和二十(shí)個家內奴隸去搶了曶的禾二十秭。曶向東(dōng)宮王太(tài)子控告匡。東宮判匡受罰。匡叩頭謝罪(zuì),用五(wǔ)田和一名農業奴隸、三名(míng)家內奴隸作抵償。曶不滿意,再次控告,一定要匡賠禾十秭,另欠十秭。如果明年不還,則要罰四十秭。後來匡還了禾,再增(zēng)加二田和一名奴隸,共七田和五名(míng)奴隸。曶免去匡四十秭(zǐ)的(de)賠償。這(zhè)則記事裏說明,“田”這個單位已成為法定單位,在法(fǎ)律訴訟中被(bèi)公認。金文中常見以(yǐ)一田、二田、七田、十田、五(wǔ)十田等為計(jì)量單位(wèi),這(zhè)足(zú)以證明“田”的畝積必定有統一的大小。
土地的分封與賦稅製有密切的關係(xì)。《孟子》雲(yún):“夏後(hòu)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ér)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貢、助、徹都(dōu)是地租名(míng)稱。貢(gòng),是自由民耕種土地,統治者依據耕地(dì)上若幹年的收獲量定出一個平均數,從平均數中抽取十分之一的貢(gòng)物。助,是自由民的耕地所有權被統治者占有,因此必須替統治者(zhě)耕種所(suǒ)謂的公田,屬於勞役地租的(de)形式(shì)。西周又把助法改為(wéi)徹法,實物地租代替勞役地租。周天子在分封諸侯時,往(wǎng)往發給他們相應的度量衡器,這些度量衡器具便成為一種權力;一旦掌握了它,便有權在(zài)所轄範(fàn)圍內征收賦稅了。
西周時期的禮儀製度(dù)十(shí)分嚴格,即“一器之設,一物之(zhī)用,莫不合王製。”而許多製(zhì)度(dù)的(de)訂立又都離不開度量衡。有了度量衡(héng),百物製度才有了(le)依據,才能立信於民。《禮記•明堂位》雲:周公“朝諸侯於明(míng)堂,製禮、作樂、頒度(dù)量而天下大服。”《禮記•大傳》又說:“聖人南麵聽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quán)度(dù)量。”西周還設置了管理(lǐ)度量衡的各級官吏(lì),如內宰、大行人、合方氏等,它們共同的任務是保證(zhèng)在周天子管轄下,統一各諸侯國的度量衡。
內容推(tuī)薦
更多(duō)>2019-11-15
2019-11-05
2019-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