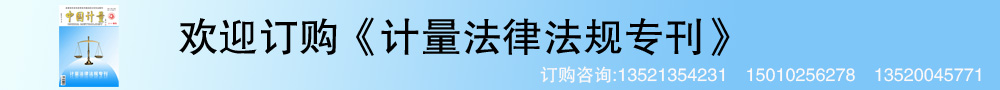
“微(wēi)禹(yǔ)吾(wú)其魚乎”。“微”在此作如果不是解。這是古人(rén)麵對滾滾黃河發出的感歎;如果沒有(yǒu)大禹治水,我們早已變(biàn)成水裏的魚蝦了,(見《左傳•昭公九(jiǔ)年》)。翻開中國的古籍,有多種、多處提到鯀和禹治水的(de)故事。
堵(dǔ)與疏
相傳三、四千年前,黃河流域發(fā)生了一(yī)次特大(dà)的水災(zāi),洪水泛濫持續了幾十年。《孟子》中說,當時到處都是白茫(máng)茫的(de)一片;洪水橫流(liú),浩浩滔天,五穀不登,禽獸逼(bī)人。以治水而著稱的共工氏,采用鏟高填低的辦法卻幾經失敗。當特大洪水威脅著人們的生存時,不得不引起部落酋(qiú)長們的高度重視。《尚書•堯典(diǎn)》說(shuō):帝(dì)堯憂於洪水泛濫。問大家誰可以治水。四嶽公推夏部落的酋(qiú)長鯀(gǔn)。《尚書•洪範》載:“鯀陻洪水。”湮是窒塞的意思。《國(guó)語•周語》又載:“有崇伯(bó)鯀……稱(chēng)逐共(gòng)工之過”。是說他不(bú)適當地沿用共工氏的舊辦法,即“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bì)以害天下。”他為了防治水(shuǐ)流,就把高處割(gē)平,低處填高,修築堤埂和土(tǔ)圍子來(lái)保護居住區和耕地。在當(dāng)時勞動(dòng)工具十分簡陋的(de)條件下,要把堤壩修築或(huò)堅實牢固,足以阻擋凶猛的洪水,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辦法終究(jiū)無法(fǎ)成(chéng)功。鯀既失敗,被(bèi)逐遠(yuǎn)出。
水患未除,治水還(hái)得另舉賢者。四嶽再推(tuī)鯀之子禹繼承其父的遺誌。禹受命治水,一方麵邀請(qǐng)契(qì)、後稷、皋陶三位氏族酋長帶(dài)領(lǐng)部落群眾加入治水行列。另一(yī)方麵又認真總結前人失敗的教訓,找出失敗的原因在於沒有察看水的流向,不了解山川澤數(shù)的自然狀況,所以不能因勢利導去排除水(shuǐ)患。《淮南(nán)子》中說:“是故(gù)禹決瀆也,因水為師。”“瀆(dú)”即水溝,“因”作依照或憑借解。又說:“決江浚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yě)。”都是說(shuō)禹治(zhì)水已總結出水往低處流的規律,依照水(shuǐ)的流向去疏通水道,加速了洪水的排泄。《尚書•禹貢》中,大致(zhì)記述了(le)禹考察和經過(guò)的(de)地域,與中國地勢西高東低的(de)走勢基本相吻合。多種史籍還記述了禹多年在外奔走,跋山涉水,探尋(xún)水源,疏通水道。《史記•夏本紀》載:禹“卑宮室,致(zhì)費於溝淢。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國語•周語》也說(shuō):“高高下下,疏川導滯(zhì),鍾水豐物(wù),封崇九山,決汨九州。”這些記載,對禹(yǔ)治水曹經實地調查,測量之事,都言之鑿鑿。綜(zōng)合許多資料(liào)可以證明,大禹治(zhì)水是有規劃,有路線並經過(guò)測量,最後把當時所(suǒ)了(le)解的疆域劃(huá)分為九州。
禹是(shì)如何去完(wán)成這樣偉大(dà)的治水和疆域劃分(fèn)工程的呢?
左準繩,右規(guī)矩
禹疏濬(xùn)水道,引水入海,首先要考察水勢,尋找(zhǎo)水的源頭和上下遊流經地域,這一切都離不開測量。規(guī)矩(jǔ)準繩就是最古老的測量工(gōng)具。《史記•夏本紀》雲:禹“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都是(shì)說一切均以勘測為主,用準定平直,“繩”測長短,“規”畫圓,“矩”畫方。“矩”還可以用來定山川之高下(xià),大地之遠近,那麽一根矩尺是怎樣來測量大地(dì)的呢?《周髀算經》開篇中假設(shè)了周公跟商高的一段問答。周公(gōng)問(wèn)商高,大意是說(shuō):天沒(méi)有台階,人不可能(néng)登上去,地這麽廣大,不可能一點點去測量,那(nà)麽測量的結果是怎(zěn)樣得出來呢?商高說:“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夫(fū)矩之於數,其裁製萬物唯所為耳。”“偃”是仰臥,指股在下,勾直立以測高,“覆”是指倒立,將矩倒立就(jiù)可以(yǐ)測深了。“臥(wò)”是平放,指測水平方向寬遠的方法。隻要探索出直角三角形的(de)性質,就可以(yǐ)摸索出對(duì)一些(xiē)不可直接測(cè)量物進行測量的辦法了。所以商高說:運用“矩”通過測算就可以(yǐ)把握萬物數量的(de)關係,這樣就可以無所不為了。故趙君卿在(zài)《周髀算經注》中說:“禹治洪水,決疏(shū)江河,望山川之形,定(dìng)高下之勢,除滔(tāo)天之(zhī)災,使東注海,無浸溺之患,此勾股之繇生也。”據他推(tuī)斷,運用矩尺的勾股原理測量距離、水平和高程,早在大禹治水時已經萌生了。《尚書•益稷》說:“(禹)予乘四載,隨山刊木(mù)。”《史記•夏本記》也說:“(禹)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刊”和“表”在此都(dōu)有刻劃的意思,都是說治水過(guò)程中,在各個測(cè)量點豎立起刻劃了一定數度的標杆,這種在(zài)高山河流處設置各(gè)種高程標(biāo)誌,有如今天大地測量技術中采用的標杆方法。
身為度,稱以出
測量離不開數和量,因此必須有記數和計量的辦法。治水這樣(yàng)大規模的測量(liàng)必定要有統(tǒng)一的計量(liàng)標準,這個標準是怎樣建立的呢?《史記》給出了答案:“(禹)身為度(dù),稱以出。”這句話(huà)可(kě)以理解為以禹的身長和體重定出長度、重量的單位。有(yǒu)了單(dān)位和標準,並把(bǎ)它複製到木棍、矩尺和準繩上,測量長度時就可(kě)以直接讀數和計算了。治水工程即使在不同地區也就可以複現和傳遞這個量了。
王(wáng)嘉在他所撰誌怪小說《拾遺記》中(zhōng)說:禹因得到(dào)神的幫助而獲得丈量工具,他在開鑿龍門而進入一個深數十裏的岩洞時,“幽(yōu)暗不可複行”,出來一頭如豕(豬)的怪(guài)獸,口銜明珠(zhū)在前麵引路,至一開豁明亮處,隻見九河神女(nǚ)華胥之子,蛇身人麵(miàn)的伏羲端坐在前。伏羲交給禹(yǔ)一支長一尺二寸的玉簡(jiǎn),使量度天地。禹即用此簡評定水(shuǐ)土。大禹治水的傳說盡管帶有許(xǔ)多(duō)神話色彩(cǎi),但它總還是一種曆史(shǐ)事(shì)實的反映。無論(lùn)是伏羲的玉簡,還是《史記》所說的禹身為度,都說明了治水是離不(bú)開度量衡(héng)的(de)。
《淮南子•地形訓》中還有一則記(jì)載:“禹乃使太(tài)章、步自東極至(zhì)於西(xī)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裏(lǐ)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wǔ)百七十(shí)五步。”大規模(mó)地治理水(shuǐ)患,必須從東到西,從南到北作初步地勘察。太章、豎亥,善行人。禹派遣二(èr)人去四方勘測,“步”便成為測(cè)量大地最原始的單位。《考工記》說:“野度以步。”這種以步為丈量土地的(de)單位甚至(zhì)延續了幾千(qiān)年。怎樣才算一步呢?《孔叢子》說“跬,一舉足(zú)也,倍跬為(wéi)步(bù)。”即一條腿跨出的距(jù)離稱“跬”,再把(bǎ)另一條腿胯(kuà)出的距離稱“步”。這些都說明了大禹治水是(shì)用(yòng)各種測量方法最(zuì)後達到(dào)治水的目的。
禹治理了水患,人民得到安(ān)居,他在部落(luò)聯盟(méng)中的威望也日益增高(gāo)。舜死後,禹成(chéng)了(le)繼承人,並建(jiàn)立了夏王朝(cháo)。從此治水時建立起來的度量衡便成為夏朝法定的製度了。
內容(róng)推薦
更多>2019-11-15
2019-11-05
2019-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