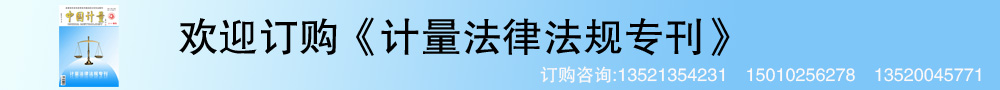春秋(qiū)戰(zhàn)國是中國封建社(shè)會初步建立的(de)時期,政治體製的巨大(dà)變化,直接影(yǐng)響經濟的變革;周天子一統(tǒng)天下的局麵開始崩潰,諸侯領地逐漸變(biàn)為私有,出現了大國爭霸(bà)的局(jú)麵。周平王東遷後(hòu),各諸侯國使用各種辦法和手段,積極發展各自的實力,新舊勢力鬥爭日益激烈,甚至度量衡也被利用為奪取政權的(de)手段(duàn)之一,其中齊國的例子最具有代表性。齊國原本(běn)姓薑,是西(xī)周薑太公的後裔,戰國時被田氏取代,雖然國號(hào)仍為齊,但政權已改由田氏(shì)家族(zú)掌管了,曆史(shǐ)上稱為“田氏代齊”。
“大鬥”與“小鬥”之爭
春秋早期地處東方的齊國,濱海而地沃(wò),有漁鹽之利。薑太公被封為齊侯後,十分重視發展經濟(jì),至齊桓公(前685~前643年)時,已成為中(zhōng)原最(zuì)早的霸主。齊(qí)桓公逝世(shì)後,隨著社會經濟的(de)發展變化和統治階級之間的爭權奪利,各種矛盾凸顯。到了齊景公(前547~前490年)繼位前後,社會矛盾已達尖銳化程度,薑姓齊國一天天走著下坡路(lù),在舊勢力日趨解(jiě)體的過程中,新興勢力逐步發展。在這種新舊勢力消長的過(guò)程中,以田氏(shì)為代表的(de)新興勢力日益(yì)壯大。
《韓非子》中有這樣一段故事:一次,齊(qí)景公(gōng)與晏(yàn)嬰同遊少海,登上觀景台,齊景(jǐng)公環視著齊國(guó)的大(dà)好河(hé)山,不勝感慨地(dì)對晏嬰說,太美了,這樣偉大、壯麗的河山,不知(zhī)將來屬於(yú)誰了。晏嬰毫不(bú)掩飾地回答:現在的薑姓齊國不久就會被田氏所取(qǔ)代。因為田氏家族(zú)深得民心,他們對(duì)上籠絡貴族重臣,對(duì)下私自用“大鬥斛(hú)、區、釜出貸,小鬥斛、區、釜收之”;“君重斂而田氏厚施”,所以民眾都扶老攜幼地投靠田(tián)氏了。盡管晏嬰如此直言進諫,卻並沒有引起齊景(jǐng)公的重視。《左傳》對這一曆史事件有更詳細的記(jì)述:公元前538年,晏嬰出使晉(jìn)國,受到上賓規格的接待,在宴會上,晉國大夫叔(shū)向趁酒酣耳熱之際,向晏(yàn)嬰討教,問起他對(duì)時政的看法,晏嬰十分感慨地說了一段話:“此季世也(yě),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戰國時,田陳讀(dú)音相近,故田氏又作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其愛之如父母(mǔ),而歸(guī)之如流水。如無獲民,將焉辟之?”類似的記載還見於《史(shǐ)記(jì)》等重要古籍(jí)中。
如前(qián)所述,春秋早期,齊國已是一個(gè)實力強大的國家,曾被列為五霸之首(shǒu)。當時齊桓公任用管仲改革內(nèi)政。管仲主張發展工商業,同時建議廢除王製,實行依法治國。還特別強調統一度量衡的政治理(lǐ)念。然而,這一思想並未引起重視。誰曾(céng)料(liào)到這種(zhǒng)失誤竟會被(bèi)田氏家族(zú)利用,成為奪(duó)權鬥爭的手段。
田氏代(dài)齊這場政治鬥爭(zhēng)絕非(fēi)一朝一夕,而是經過幾代人的耕耘,一(yī)百多年的時間才取得成功。度量衡在這場鬥爭中一直起著十(shí)分重要的作用卻是(shì)不(bú)可回避的事實,故事還(hái)得從頭說起。田氏是春秋時(shí)期陳國厲公(公元前706~前700年)的後代,陳厲(lì)公(gōng)的兒子叫陳完。相傳有一次,周國的太史路過陳(chén)國,陳厲公就(jiù)請他為子孫們占卜,太史看完卜兆後說,陳完的子(zǐ)孫有取得國家的可(kě)能,但不都是陳國而是薑姓齊國。後(hòu)來陳國(guó)發生了叛亂,陳完就逃出了陳國來(lái)到(dào)了齊國,這時正是齊桓公四年。齊(qí)桓公要立他為相,陳完推辭說,我是逃難在外(wài)的人,哪能(néng)占據這樣(yàng)高(gāo)的(de)位置呢?齊桓公就讓他當了工正(管(guǎn)理工商業的官吏),並改叫田完。從此田氏便在齊國站穩了腳跟,並逐漸成為新興勢力的(de)代(dài)表。他們采(cǎi)取一係列措施(shī)進(jìn)行各種改革,並展開與以齊國國(guó)君為(wéi)代表的舊勢力的鬥爭。到(dào)了(le)齊景(jǐng)公時代,貴族奴隸主對平民殘(cán)酷的壓榨、無情的(de)殺戮,致使(shǐ)受刖刑(xíng)(一(yī)種酷刑(xíng),砍掉一隻腳)的人多致使齊國“市”上草鞋跌價而義足漲(zhǎng)價,哀鴻遍野,民(mín)不聊生(shēng)。另一方麵(miàn),田氏(shì)家族已經過多代人的慘(cǎn)淡經營(yíng),傳到田僖(xi)子時代,家族勢力更加壯(zhuàng)大。田氏即(jí)趁民不(bú)聊生之時機,向民眾施以小恵,竟無視官府的禁令,私設“家量”。當民眾遇到災荒或繳不(bú)上賦稅而向他借貸時,常常用“家量”(大鬥)借出,以“公量(liàng)”(小鬥)收回,正是以度量衡為手段,籠絡了人心,同時也是與貴族舊(jiù)勢力相抗衡的一種手(shǒu)段。田(tián)氏的這種(zhǒng)做法引起了晏嬰(yīng)的高度重視,他力諫齊景公,希望貴(guì)族們不要太奢侈,減輕(qīng)民眾的賦稅。齊(qí)景公非但不聽,還把晏嬰打(dǎ)發到晉國(guó),這才有晏嬰與叔(shū)向的談話,在酒過三巡後發表了上述一番言論。
田氏代齊(qí)並統一(yī)度量衡
齊(qí)景公逝(shì)後,齊國又因統(tǒng)治階級內部發生鬥爭,田僖子趁機當上了國相,開始執掌了齊(qí)國大權。田僖子(zǐ)逝,田成子立為相時(shí),感到奪取齊國政權之(zhī)時機已到,一方麵效(xiào)仿前輩們以大鬥借貸小鬥收回的手段籠絡民心,把廣大民眾聚集到自己身邊;另一方麵他還大力發展(zhǎn)經濟,在田氏管轄的範圍內整頓物價 ,繁(fán)榮市場。據史書(shū)記載,當時在田氏采邑內,山裏出的竹木、海裏產的魚蝦十分豐富,而(ér)且價格(gé)還很(hěn)便宜,與國君控(kòng)製的地區形成鮮明的對(duì)比,百姓歡呼著田氏“愛之如父(fù)母,歸之(zhī)如流水”,田氏家族的勢(shì)力已足夠壯大。至公(gōng)元前404年,終於用武力(lì)奪取了薑姓齊(qí)國的政權,史稱田(tián)齊。在長達(dá)一百多年的時間裏,田氏家族始終(zhōng)利(lì)用以家量貸,以公(gōng)量收的辦法。在取得政權後,又立即以“家(jiā)量(liàng)”為全國統一(yī)的度量衡製度,徹底廢除了舊時齊國的“公量(liàng)”,這一事實可以從出土的器物中得到證實。1857年,在齊國故地山東出土了置(zhì)於“左關”地方征(zhēng)收賦稅的三件大型量器:“子禾子銅釜”、“陳純銅釜”、“左(zuǒ)關銅 ”。經過實際測量,銅 容2070毫(háo)升(shēng),兩件(jiàn)銅(tóng)釜分別容20460毫升、20580毫升,正是十進(jìn)位製(zhì)。此外,近(jìn)幾十(shí)年,在齊國故地出土了一些(xiē)量器,其中(zhōng)有6件型製相(xiàng)仿的(de)銅量(liàng),其容量皆合當時的5升和10升,而在臨(lín)淄出(chū)土的多件陶量中,有兩(liǎng)件(jiàn)自銘為“ ”(升(shēng)),約合209毫升(shēng),約相當於“銅 ”的十分之一。“ ”很可能是一(yī)鬥(dòu)的容量。
綜上所引史書以(yǐ)及實物互為佐證,可對齊國容量製(zhì)度作如下分析:齊國(guó)早在春秋時期已有一套完整的容(róng)量製度:①4升=1豆、4豆=1區、4區=1釜、10釜=1鍾;②齊國除(chú)了有全(quán)國通行的“公量”製外,田氏還自立了一種“家量”,家量比公量大了五分之(zhī)一,由(yóu)於“家(jiā)量”未被禁止,常常在陳氏(shì)家族認為(wéi)有必要時(shí)與“公量”並用;③齊國舊有的“公量”是豆、區、釜、鍾製,皆為四進位,釜至鍾為十進位;田氏代齊後,量製已采用當時在各國(guó)比較(jiào)通行的升、鬥、斛製,改四進為五進位,並逐步形(xíng)成(chéng)升(shēng)、鬥、釜(斛)十進位製,最後廢除了齊國的舊製,並與(yǔ)其(qí)他各諸侯國基本保持(chí)一致。所見齊國量器多為戰(zhàn)國後期,故皆多為十進位製(zh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