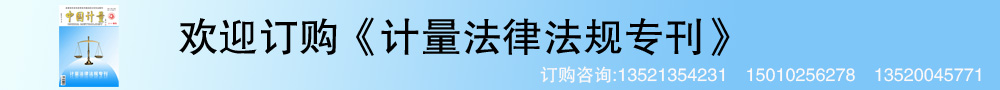度量衡這一稱謂,最早見(jiàn)於(yú)《尚書·舜典》:“同律度量衡”。度量衡除了作為長度、容量、重量的簡(jiǎn)稱外,還應該包括單位、製度和一切管理條(tiáo)例。本文僅簡單地介紹古代(dài)度量衡單位名(míng)稱的由來與(yǔ)趣事。
寸、尺、丈
《說文解字注》(以下(xià)簡稱《說文》)雲:“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體為法”。《大戴禮記》、《孔子家(jiā)語》中都有:“布(bù)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的記(jì)載。《小爾雅》中還說:“跬,一舉足也,倍跬為步”(古代一步為(wéi)六(liù)尺)。這些都是以人體為度量衡單位的記載。《說文》中,尺字寫作“

”,可與“布手知尺”互為佐證,即一尺為成年人拇指與食指伸(shēn)開的距離與形狀。
今天的一市尺長33.3厘米,無論如何與“布手知尺”的長度不相符。而《大戴禮記》、《說文(wén)》的(de)作者是漢代人,《孔子家語》的作者是魏晉人,西漢至晉一尺(chǐ)皆長23.1~24厘米之間,與“布手知(zhī)尺”不合。難道這些都是後人杜撰的嗎?並(bìng)非如此(cǐ)。古人治學是十分嚴謹的,那麽,“布手知尺”之說有沒有根據呢?有幸的是,今國家博物館和上(shàng)海博物館各藏有一支商代象牙尺,尺長約16厘米,尺上有分、寸刻度,均為十進位。對(duì)此我們作了一個驗證,身高在160厘米者,拇指至食指之間距(jù)離為(wéi)16厘米,一指之寬為1.6厘米。考古學家李(lǐ)濟先生在1921年對當時中國人身高測量作了一個統計,成年人身高平均為164~165厘米。此外,由考古(gǔ)發掘證明的古人身高:女子為150~160厘米,男子為160~165厘米(mǐ)可證,“布手知尺”說是有根據(jù)的,隻是商代以後,尺度增長而造成與此說不合的結果。
《說文》中“寸”字寫作“

”,寸字下雲:“人手卻動脈謂之寸口從又、一。”而“又”字寫作“

”,並解釋說“又,手也(yě)”。像人手伸出三指狀。寸字就(jiù)是在手下加了一橫。“人手卻動脈謂之寸口”這句話(huà)是(shì)形容中醫用食指按脈狀。“卻”作“退”解,是說雙手十指並攏(lǒng),退至手腕處正是一指按脈處。丈字寫作“

”,即在又字上加十,故曰:“丈,十尺也”。如果我(wǒ)們用自己(jǐ)的身高和雙手(shǒu)去做個試驗,就可以證明《說文》對字的結構和解釋是十(shí)分嚴謹的。
《史記·夏本紀》中有關禹“身為度(dù)”的記載,但(dàn)沒有明確的數字可供參考,故後人(rén)對此有不同的理解,有說禹身長(zhǎng)九尺二寸;有說九尺(chǐ)五寸;還(hái)有說九尺(chǐ)有(yǒu)咫……朱載堉在《律學新說》中說到“諸家各異(yì),莫之適從……以理論之,若據身為度之一言,則應長十尺為是,蓋十尺(chǐ)為一丈,古稱丈夫(fū)”。我們主張以朱載堉(yù)之說為是,商尺長16厘米,應該正是夏尺的延續。
用人體(tǐ)來定長度,世界許多古老文明的國家皆有相關的記述,古(gǔ)希臘哲學家普羅塔戈爾有句名言:“人是萬物的度量衡”。而《孔子家(jiā)語》中:“布指知寸,布手(shǒu)知(zhī)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說(shuō)得更加具體,更有可操作性。世界(jiè)各個(gè)民族的先人,最初的測量(liàng)活(huó)動往往(wǎng)都是(shì)借助於人體器官來實(shí)現的,如手、指、腕、足(zú)以及人體(tǐ)的自然(rán)身高等。如肘尺(又譯(yì)作腕(wàn)尺),是古老的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時期的長度單位,大約出現於公元前6000年,這個單位的概念是,伸開手臂,從肘關節至中指間(jiān)的距離。在公元前2500年(nián),古巴比倫(lún)尼亞王國的長度單位有“指”,一指相當於1.65厘米,一尺(chǐ)是(shì)20指(zhǐ),一腕尺等(děng)於30指。而在南美洲文明較早的印加帝國(guó),長度單(dān)位是162厘米(mǐ),相(xiàng)當於古代秘魯(lǔ)人的平均身高。《英國(guó)度量衡史》一書中也提到,原始的計量單位是指、掌、噚(xún)。一噚大約等於一人的身高,一呎大約等於六分(fèn)之一噚,一(yī)拃為(wéi)八分之一(yī)噚。一個(gè)人的步(bù)距大約是半噚。用人體定度量衡單位(wèi)甚至延續到16世紀的西方許多國家。十世紀時,英(yīng)王埃(āi)德加曾以其拇指關節間(jiān)的長(zhǎng)度定為一吋;查理大帝以其足長定為(wéi)一呎。根據十六世紀德國的規定,英尺的另一(yī)個定義是以(yǐ)某一個星期日禮拜完畢後,令最(zuì)先走出教堂的16名男子(zǐ),立於(yú)教堂門前,高(gāo)矮不拘,隨意而定,各出(chū)左(zuǒ)足,前後相接,取得此長度的十六分之一為(wéi)一法定單位。而一碼則曾以英王亨利一(yī)世鼻尖至手(shǒu)指間距離而定。如(rú)果從解剖學的觀(guān)點來看,人體各部位具有(yǒu)完美的比例,如一指為寸,十指正(zhèng)相當於伸出大拇指和(hé)食(shí)指的這段距離。一拃為一尺,人的(de)身高正好相當於它(tā)的十倍。人體的(de)身高又與(yǔ)伸出兩臂之長(zhǎng)相等。人(rén)體這一完(wán)美的比例關係,歐洲十五世紀的(de)藝術解剖學中常(cháng)用繪畫表(biǎo)現出來。
吃一豆肉、喝一豆酒
容量單位(wèi)最初也與人體有(yǒu)著密切(qiē)的關係,如用手捧物作為一個單位(wèi),即(jí)“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等,後來借鑒一些日常生活(huó)用具。如《考工記》中有“食一豆肉,喝一豆酒,中人之食也(yě)”。由於豆的容(róng)量適中,使用方便,逐漸被轉化為一個專業的容量單位了。《左傳》中說(shuō)到齊國的量器(qì)有:豆、區(qū)、釜、鍾。這些原來都是一些日常用器:“釜”是烹飪用的大鍋,“鍾”是(shì)古代大型的盛酒器,從出土(tǔ)的戰國量器中,還可以看到不少仍保留著適用器的器(qì)形,如齊(qí)國的子禾子釜、左關钅和(hé)、楚國的銅量等,直至戰國(guó)後(hòu)期,才逐漸形成(chéng)比較固定、便於使用的專用的量器器形,並且名稱也從豆、區、釜、鍾等這類(lèi)借用名(míng)轉化(huà)為升、鬥、斛等專(zhuān)用名稱了。
由於十進位的升、鬥、斛這些單位(wèi)直至戰國後期才逐漸形成,而更早期的容量製度既不見實物,又缺乏係(xì)統(tǒng)的文字記載,散落在各種古籍中的單位和進(jìn)位關係,經後人整理、注釋,也就很(hěn)難取得一致看法,如(rú)《小爾雅》雲:“一手之(zhī)盛謂之溢(yì),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但(dàn)掬(jū)還有二升、四升(shēng)不同說法,戰國時(shí)一升(shēng)合200毫升,那(nà)麽兩手捧米的容(róng)積最多也隻能是一升,故(gù)一掬二升、四升之說皆與實際情況不合。
再舉(jǔ)一例,古籍中常見有庾這個單位,有(yǒu)說1庾等於24升,有說1庾等於160升。戴震在(zài)《考工記圖》中力主1庾等於24升說,他引《論語(yǔ)》中的一(yī)個故事作佐證;孔(kǒng)子派子華去齊國出差,家中僅有(yǒu)一老母無人照料。冉子不放心,就到孔子處為子華的母親(qīn)申請一些糧食作為補助。孔子說你給她送去一(yī)釜吧,冉子覺得少了,孔子說,那(nà)就(jiù)再加一庾吧!據此戴震認為,原來給一釜(64升),再加一些不可能(néng)比原來多出兩倍有餘,因此認為一庾 應該是24升,而不可能是160升。
古(gǔ)籍中(zhōng)還記述了一些相當大的容量單位,如《儀禮·聘禮》中雲:“十鬥曰斛;十六鬥曰籔;十籔曰秉;(秉(bǐng))二百四十鬥。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bǎi)秉為一秅”。從這一(yī)段文字看,前後文(wén)有訛脫(tuō)。曆代考古學家皆對當時能否有如此大的容量單位表示懷疑(yí),多認為斛以(yǐ)上不可能是(shì)容量單位,而是表示禾稼的計數(shù)單位。《詩經》中有“彼有遺秉(那邊有遺(yí)餘的禾把)”,“此有滯穗(這裏有(yǒu)遺漏的穀穗)”,可證此秉不(bú)會是容量單位(wèi)。故孔穎達說:“禾(hé)之穗,一把也,米之秉16斛也;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jǔ)則五鬥”。
用“把”計禾稼,還可以從少數(shù)民族的習慣(guàn)中得到佐證。據(jù)報道,貴州台江縣苗族農民,在收割稻穀時,以一手所握為一“把”;兩(liǎng)手為一“非”;十“非(fēi)”為一“庋”。在度量衡製度還很不完備的先秦時期,出現許多不合規範的單位並不為奇,後人又根據各自的理解作出不同的(de)解釋,造成了古代文獻(xiàn)中許多(duō)爭議也是正常(cháng)的(de)。對其中還存在爭議的單位,我們今天也不必過(guò)多去深究了。
斧與斤
重量單位起源(yuán)於什麽時代尚不能確(què)證,我(wǒ)們(men)先從鈞、石這兩個單位(wèi)入手作一些探討。《說文》石字下(xià)雲:“石(shi),山石(shí)也”。段玉裁注:“或借為碩大,或借為

字,(今約定俗成(chéng),也讀作石dan)

,百(bǎi)二十(shí)斤也”。段玉裁(cái)將“石”加偏旁“禾”是很有道理的,目前所見戰國120斤石權,往往都(dōu)是(shì)作為稱糧食和芻草之(zhī)用。《漢書·律曆誌》對“石”作了如下解釋:“石,大也,……四鈞為石(shí)”(一鈞為30斤),與《說文》中:石“百二十斤也”正(zhèng)合。這些都是指戰國至秦漢時的製度。“石”作為重量單位,戰國(guó)銅權刻銘上就常常會見到,與同時期的“斤”權相比較(jiào),也正好合120斤。此外,戰(zhàn)國(guó)時期的文獻中也(yě)多次出現石、鈞(jun1)這些單位,至(zhì)於更早的夏商周時期是(shì)否已有相對的單位呢?目(mù)前隻見《夏(xià)書》曰“關石禾鈞,王府則有”。據史學家們分析研究,認為這裏說的石、鈞應該是重量單位。而我們認為,夏代未必已(yǐ)有這些與後代完全相對應的石、鈞一類的重量單位,但是已有度量衡器並置於王府則是可信的。西周(zhōu)青銅(tóng)器上常見(jiàn)“金一勻”、“金十勻”一類的(de)刻(kè)銘,證明西(xī)周已用“勻”作重量單位了,隻是此一勻的實際重量是否與戰國、秦時相同(tóng)已不得而知了。
從鈞和石的含義來看,先人們對這兩個重量(liàng)單位(wèi)是(shì)早有認識的,鈞還有用肩挑物之意,鈞是平均,即人挑重物時,兩端分(fèn)量必須相等,才(cái)能保持平衡。人類在生活中長(zhǎng)時間積累的經驗(yàn)證明,用肩(jiān)挑運重物是一種有效的方法,久而久之發展(zhǎn)成了“天平”。迄今(jīn)所見我國(guó)最早的砝(fǎ)碼屬於春秋時期,而其中大(dà)部分則出土(tǔ)於戰國時期的墓葬(zàng)中,故對此之前夏商周三代衡器狀況知之甚少。甲古文中有“

”文,似人用肩挑物狀。而公元(yuán)前1567~前1320年(nián),埃及(jí)十八王朝時代墓葬(zàng)的壁畫中也記錄了人們用肩挑魚的圖形。地(dì)中(zhōng)海古希臘(là)邁錫尼(ní)諸(zhū)國,在公元前15~前12世紀,已用“

”的符號來表示重量單位(wèi)。這些都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權衡器中的天平,很早就在世界各國(guó)被廣泛使(shǐ)用了。
“斤”這個單位也是從實用器中轉化而來的。《說文》雲:“斫木斧也,象形”,寫作“

”。段玉裁注曰:“橫者象斧(fǔ)頭,直者象柄,其下象所斫木”。“斧(fǔ)”輕重適中,久而(ér)久(jiǔ)之便轉借為(wéi)一個重量的基本單位了。
“兩”《說文》寫作“

”“平分(fèn)也”。《淮(huái)南子(zǐ)》雲:“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gù)二十四銖為(wéi)一兩”。這些都是針對杆秤尚未發明之前,稱物時兩端載重必須相等的天平而言。
本文刊發於《中國計量》雜誌(zhì)2011年第(dì)6期。
《中國計(jì)量》雜誌社官方唯一論文接收郵箱:chinametrology@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