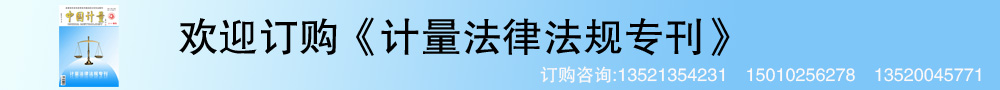

史先生和他收藏的地契。
你知道最小(xiǎo)的長(zhǎng)度單位和麵積單位嗎?
昨天上午,南京高淳區(qū)椏溪(xī)鎮椏(yā)溪(xī)村中村一位居(jū)民,向揚子(zǐ)晚(wǎn)報記者展示了一張清(qīng)代地契,裏麵對土地的描述竟然十分精確。
這張代代相傳的地契上,除了畝和毫厘(lí)等我們耳熟能詳的單位,還出現了有“絲”和“忽”。相關曆史資料顯示,清代(dài)及以前,有關長度及(jí)重(chóng)量的(de)記錄,竟然精確到了百萬(wàn)億(yì)分之一。專(zhuān)家表(biǎo)示,這些“超細微”單位(wèi)最早始於漢代(dài),於細(xì)到百萬億分之一是因為古人(rén)沒有有效數(shù)字的概念。 揚子晚報記者 梅建明 文/攝
百(bǎi)年收藏
高淳發現清代地契 藏在梁下(xià)保存至今
今年70歲(suì)的史(shǐ)先生,是土生土(tǔ)長(zhǎng)的(de)南京(jīng)高淳椏溪村中(zhōng)村(cūn)人,正是(shì)他收藏了這些地契。
見到(dào)揚子晚報記者,史(shǐ)先生(shēng)小心翼翼地從木箱裏拿出個紙包。打開紙包,是10多張發黃(huáng)破舊的地契。仔細看,除(chú)了(le)一部分因為保存原因出現些許(xǔ)破損,大部分完好。
史先生表示,由於(yú)這些地契用的都是比較好的宣紙,這才能保存到今(jīn)天。揚(yáng)子晚報記者了解到,如果從立地(dì)契的年代算起,這些地契已(yǐ)經有百餘年的曆史了。這些(xiē)地契裏(lǐ),最早的可追溯到清光緒十一年,距現(xiàn)今(jīn)有近130年了。
史(shǐ)先生說,這些(xiē)地契反映了爺爺那一輩人家庭生(shēng)活的曆史。爺爺去世後(hòu),父親便將這些地契保(bǎo)存下來,並傳給了自己。據史先生回憶,很小的時候,父親(qīn)就告(gào)訴他,祖輩們通過辛苦勞作,攢錢買田買地,在當地也是小有名氣的富戶。
史先生18歲的時候,父親臨終前將這些地契交到他手中,並交(jiāo)待要好好保存(cún),將來也要傳給下一代,主要是讓後(hòu)代更(gèng)加了解祖輩辛(xīn)苦打拚才能擁有田地的曆史,也好讓後代知道(dào)創(chuàng)業之艱。
史先生稱,這些地契在自己手裏已經保存了52年,以前家裏住的是草房(fáng),因怕被雨淋濕地契(qì),他特地用(yòng)油皮紙緊密包裹起來,並吊(diào)在屋梁下,即便有雨淋一點,也被屋梁擋住了。後來(lái)搬到樓(lóu)房裏住,他又(yòu)把地契藏(cáng)到木箱裏,輕易不(bú)示人觀看。
史先生表示,自己有兩個兒子兩(liǎng)個女兒,這些地契(qì)是祖上傳下來的寶(bǎo)貝,他打算交由兒女們保存,以後也像父親交(jiāo)待的一樣,代代相傳下去。
千年探秘
“六毫二絲五忽(hū)”的地(dì),到底怎麽劃?
揚子晚報記者在(zài)史先生收藏的地契上看到,地契最上方(fāng)印有(yǒu)“清丈執業印單”字樣,並標有良田的圖形麵積。此外,毎張右側都印著“欽加同知銜特授溧陽(yáng)縣正堂曹”,左下角還有戶業史誌創的名字,以及模糊的官府紅(hóng)印章。
其中(zhōng)一(yī)張(zhāng)地(dì)契上,可以看(kàn)到清晰的“淸光緒二十七年”字跡(jì),並注明了是史誌創與蔣許生雙方買(mǎi)賣田地的契約(yuē),田地的麵積為“壹畝叁分伍厘陸毫貳絲伍忽”。
據史先(xiān)生介紹,他們村東有個仁字門(mén)村,以前屬溧(lì)陽,曾經也劃給高淳,後來又劃歸溧陽。而地契(qì)中的史誌創,正是他的爺爺(yé),當(dāng)年他爺爺就住在仁字門(mén),地契中的溧陽縣正堂(táng)也是指(zhǐ)的溧陽府銜。“這些地契也是當年爺爺與別人買(mǎi)賣田地留下的,經過了當地溧陽(yáng)府銜(xián)的批閱。”史先生說,地契中的厘毫絲忽標(biāo)得如(rú)此詳細,也(yě)說明了(le)當時地契(qì)買賣顯得(dé)公平(píng)公(gōng)正。
南京市計量監督檢測院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一畝三分地”是(shì)一句俗語,但也反映在較早的年代裏,田(tián)地的單位基(jī)本是以畝為單位,下麵細到分基本就到位了,再細化到厘,隻是字麵概念。“像這樣精確的地契實屬少見。”
十萬億分之一的銀子(zǐ),到底(dǐ)怎麽給?
我們通(tōng)常聽到“差之毫厘,謬以千裏”的說法,印(yìn)象中的“小單位”應該是“毫”。按照(zhào)現在地契上的記載(zǎi),“毫”後麵更小的(de)單位是“絲”和(hé)“忽”,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南京一位研究明清曆史的專家(jiā)告訴記者,他經常聽(tīng)到(dào)過“細於發絲”的說法,自己也以為這“絲”是一個比喻,形(xíng)容比頭發絲還細,沒想到這“絲”居然還是一個計量單位,因為沒有(yǒu)接觸到相關的(de)史料,他也沒有聽說過(guò)“忽(hū)”也是計量單(dān)位,甚至是比“絲”還小(xiǎo)的單(dān)位。“中國古人是聰明而厲害的,考慮得這麽細,我(wǒ)疑惑的是,細到這個地步,有用嗎?”這位專家笑著告訴記者,這些(xiē)有趣的現象屬於偏門,關注的人少之又少。
揚子晚報(bào)記者查閱了(le)相關資料,發現了更令人驚奇的現象:從清代山東《招遠縣誌》中,有讓人咋舌的精確記錄。在《賦役》篇中(zhōng),有(yǒu)田畝及人丁賦稅的分配,“盛世滋生增益人丁叁(sān)萬伍幹貳百捌拾壹丁,欽奉恩詔,永不加賦”,記錄有(yǒu)“該(gāi)折地伍頃捌拾伍畝叁厘陸毫叁絲伍(wǔ)忽叁微”,比起高淳現存的地契(qì)更精進一步,從“忽”到了“微”。從征收(shōu)賦稅銀兩的記錄來看,“起運地丁銀壹萬肆(sì)千肆百貳拾(shí)肆兩捌錢伍(wǔ)分柒厘(lí)陸毫陸絲貳忽柒微壹纖陸沙柒(qī)塵捌渺壹漠伍埃捌溟”,直看得人眼花繚亂。
此外,在清(qīng)康熙年間(jiān)福建的《連城縣誌》上也有同樣的記載(zǎi),讓人(rén)歎為觀止。
專家(jiā)解釋 古人刻板認真,算到多少位就(jiù)寫多少位
揚子(zǐ)晚報記者發(fā)現,古代計量(liàng)單位,不管是麵積還是(shì)重量,兩者除在前麵的大數上有區別外,後麵的小數單位(wèi)基本(běn)相同。
比如“起運地丁銀壹萬肆千肆百貳拾肆兩捌錢伍分(fèn)柒厘陸毫陸(lù)絲貳忽柒(qī)微壹纖陸沙柒塵捌(bā)渺壹漠伍埃捌溟”,居然精確(què)到了小數點後14位,改用小數點計數法應該為(wéi)“14424.85766271678158兩”,等同於十萬億分之一級別。計量這樣的銀兩,現代人都難之又難。
對此,上海交通大學古代計量科(kē)學曆史專家關增建教授表示,古代如(rú)此記錄,這樣的精度既無(wú)必要,也(yě)測量不出(chū)來。“當時的測量工具根本到不了這樣(yàng)的精度,造成(chéng)這種局麵有兩(liǎng)個原因。”
關教授稱,一是中國古代沒有(yǒu)類似現在的小數(shù)點方法(fǎ),古人或者用(yòng)分數表(biǎo)示很小的數,或者用計量單位來表示很(hěn)小的(de)數,這個傳統從漢代(dài)就(jiù)有了。此外,古代人沒有有效(xiào)數字(zì)概念,這導致他(tā)們計(jì)算結(jié)果是多少位就寫多少位,從而使記錄結果達到了匪夷所思的地(dì)步。
“至於計量單位重量與麵積如何區分,這主要看該單位是用於測(cè)重,還是用於測麵積,後麵的小單位因為(wéi)無實(shí)際意義(yì),所以長度、麵積(jī)、重量(liàng)等的小單(dān)位名稱上多有重合,是不奇怪的。”關教授告訴記者,從這種意義上說,這可以算是中國古代(dài)文化中的一個有趣的現象,記錄(lù)如此細致,表(biǎo)明我們先人刻板認(rèn)真的(de)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