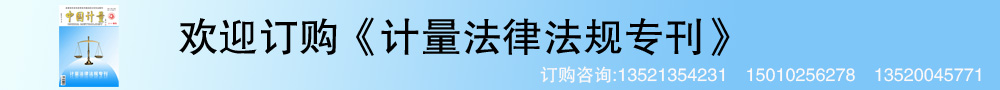
一生獻身科學 心係國家安危
祖衝之(zhī)字文遠,生於劉(liú)宋元嘉六年(公(gōng)元429年),祖籍範陽郡(jun4)遒縣(今(jīn)河北淶源(yuán)縣)。西晉末年,北方發生大規模(mó)戰亂,祖衝之的先輩從河北遷徙到江南(nán),並在江南定(dìng)居下來。祖衝之就出生在江南,其祖父祖昌任劉宋朝大(dà)匠卿(qīng),是朝廷管理土(tǔ)木工程的官吏,父親祖朔之做“奉朝請(qǐng)”,學識淵博,很受時人敬重,常被邀請參加皇(huáng)室的典禮、宴(yàn)會。祖衝之一生曆經南朝的宋(公元420~479年)和齊(公元479~502年)兩個朝代,從小就(jiù)受到很(hěn)好的家庭教育。爺爺給他講“鬥轉星(xīng)移”,父親(qīn)領他讀經書典籍(jí),家庭的(de)熏陶,耳濡目染,加之自己的勤奮,使他對自然(rán)科學和文學、哲學,特(tè)別(bié)是天文學(xu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qù),在青年時代就有了博學的名聲。25歲(suì)時,他(tā)進入劉宋孝武帝創設的學術機構——“華林學省”,誦讀(dú)儒家經典,給《論語》、《孝(xiào)經》等儒家經典作注釋,還努力學習曆代的和(hé)外國傳入的科技成就。宋大明五年(公元461年),祖衝之在南徐州(現鎮江)刺史(州地方長官)手下做從事史,後又任司徒府公(gōng)府參軍,這些都是幫助長官辦事的(de)小官。他利用工作的餘暇(xiá),集中精力鑽研與計量有關的天文、曆(lì)法和數學。這(zhè)時他正當30來歲,就製定出了當時最精密的曆法——大明曆,並在圓周率的(de)推算方麵(miàn),取得當時世(shì)界上最好的結果。公元464年,他被調到婁縣(今昆山)任縣令。南宋(sòng)末(mò),回到建康(今南京)做謁(yè)者仆射,這是掌管朝廷宴會、典禮禮節的官職。這時,他的研究興趣,又轉移到了機械方麵,重造了指南車。祖衝之50歲的(de)時候,南宋政權被齊(史稱南齊)取代。在齊高帝蕭道成和他的(de)兒子齊武帝蕭頤統治期間(公元479~493年),南(nán)朝經濟和文化繼續得到發展。在這種社會環境下,祖衝之專心研究機械,發(fā)明了“千裏船”,還(hái)製造了(le)水碓磨等糧食加工器具。
祖衝之的晚年,正是南齊的後期。在(zài)當時(shí)社(shè)會內憂外患的情況下,祖衝之在潛心科學研究的同(tóng)時,也(yě)關(guān)心著國家的安危,努力探討治國安邦之(zhī)策。他晚年被提升為(wéi)長水(shuǐ)校尉(禁衛軍將官(guān)),在任軍職期間,他上書《安邊論》,主張“開屯田,廣農殖”,他的(de)建議受到(dào)齊明帝的重(chóng)視,明帝打算派他巡行四方,興辦利(lì)民工程,但(dàn)因連年戰(zhàn)爭,終(zhōng)未有果。而這時祖衝之已經是(shì)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了。齊永元二年(公元500年),祖(zǔ)衝之這位一(yī)生勤奮憂國的偉大科學家溘然去世,享年72歲(suì)。
[page_break]
重視測量精度 搜集保存古尺
祖衝(chōng)之在其一生(shēng)的科學實踐中(zhōng),為了窮盡物理奧密和探索自然規律,極端重視對事物的仔細觀察和精確測量(liàng)。
在給(gěi)宋孝武帝請求頒行《大(dà)明曆》的上(shàng)表中,祖衝之提到,他在治曆(lì)實踐中,“親量圭尺,躬(gōng)察儀漏,目盡毫厘,心窮籌策”。自己動手測量圭(guī)表上的日影尺寸,觀察儀漏刻度,目測到毫厘,對測(cè)得的數據用心計算分析,以明白其中奧妙。他自稱在測量和處理各類(lèi)數據時的(de)主導思想是“數各有分,分之為(wéi)體,非細不密”,“深惜毫厘(lí),以全求妙之準;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意思是:測量(liàng)中所得數據都代表一定的量,要把這些(xiē)量搞準確,測量數據必須精密,因此他在測量(liàng)中特別重視小到毫厘(lí)那樣的單位量,目的是為了達到結果的全麵準(zhǔn)確;做大量艱苦的工(gōng)作,為的是確立一個永久的製(zhì)度。對測量的(de)精度和準確程度的重視,使他在天文、數學領域最終做出了(le)令(lìng)人景仰的成就(jiù)。
中國古人有個傳統認(rèn)識:為了保證曆代天文測量(liàng)數(shù)據的承傳一致,必須研究(jiū)各個時期尺度值(zhí)變化的情況。為此,很多天文和音律學家都(dōu)力求找到(dào)古(秦漢)製的標準尺度。在這方麵,晉代律曆學家荀勖之所為頗有代表(biǎo)性:荀勖按(àn)照晉武(wǔ)帝的指令考訂音律,發現當時的尺度比古尺長了4分多,他據此製作了新的符合古製的(de)尺子,該(gāi)尺被稱作荀勖律尺,公認為古尺度標準。《晉書·律曆誌》對之有詳(xiáng)細(xì)記載。荀勖律尺(chǐ)在東晉時即已銷聲匿跡,但經過一百多年後的劉宋時期,卻又輾轉被祖衝之發現,經過祖衝之的宣(xuān)傳和介紹,這才重新為人所(suǒ)知,以至於人們把它稱之為(wéi)“祖衝之所傳銅尺”。
祖衝之是如何保存並傳遞荀勖律尺的,我們一無所知。導致我們作出上述判斷的,是唐代李淳風在考訂曆代尺度時,對“祖衝之所傳銅尺”的記載。該記載詳見於李淳風所著的《隋書·律曆誌上》,原文為:
祖衝之所(suǒ)傳銅尺。
……梁武《鍾(zhōng)律緯》雲:“祖衝(chōng)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jìn)泰始十年,中書考古(gǔ)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hú),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ruò),其餘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雷次宗、何胤之二人作《鍾律圖》,所載荀勖校量古尺文,與此銘同(tóng)。而蕭吉《樂譜》,謂為梁朝所(suǒ)考七品,謬也。今以此尺為本,以校諸代(dài)尺雲。
李淳風研讀祖(zǔ)衝之所傳銅(tóng)尺(chǐ)上的銘文後,斷定它就是荀勖所製訂的律尺,並以之為(wéi)標準,對前代諸多尺度作了(le)校核。就銘文而言,該尺是荀勖律尺,斷無可疑,但(dàn)該尺(chǐ)是否即為祖衝之所傳呢(ne)?李淳風的依據是梁武帝《鍾(zhōng)律緯》的記載,梁朝上承南齊,祖衝之晚年是南齊重臣,他去世兩年而梁(liáng)武帝即位,所以梁(liáng)武帝對他的記述應(yīng)該是可靠的,該尺確實是祖衝之(zhī)所傳。
祖衝之能搜羅(luó)到該尺,很不容易。因為荀勖律尺本來就隻用於考訂音律,社(shè)會上鮮見其蹤跡,更何況西晉末年,戰亂大起,京城洛陽被(bèi)石勒占領,晉朝皇室匆忙南遷(qiān),各種禮器遺失殆盡。《隋書·律曆(lì)誌上》對此描繪說,“及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荀勖律尺當(dāng)然(rán)也難逃厄運。在這種情況下,他要搜尋(xún)到荀勖律尺,其難度是我們無法想(xiǎng)象的。這(zhè)件事情,充分表現了祖衝之對求索古製標準尺度的重視。
《隋書·律曆誌》中關於祖衝之圓周率的記載
[page_break]
推算圓周率值 考校新莽嘉量
漢代以前,圓周率一直采用(yòng)“徑一周三”。這一數值很不精確。隨著生產和科學的發展,漢代一些學者開始(shǐ)探求比較精確的圓周率值。從新(xīn)莽嘉量可得出西漢末劉歆所采(cǎi)用(yòng)的(de)圓周率(lǜ)為3.1547,東(dōng)漢末的張衡則采用(yòng)π=≈3.1623,三國時期吳人王蕃得出π=3.1556的數值。但他們求圓周率,都是以經驗為基礎,沒有科學的論證。魏晉之際,傑(jié)出的數學家(jiā)劉徽創立了“割圓術”,他(tā)用這一方法分割到圓內(nèi)接(jiē)正192邊形時,得出π值等於3.14124,後來又求得圓內接正(zhèng)3072邊形(xíng),得出π值等於3.1416。祖衝之並不滿足於劉徽(huī)的結果,他希望(wàng)求(qiú)得更精確的圓周率值(zhí)。要推算更精確的圓周率(lǜ)值,劉徽的(de)“割圓術”是個(gè)很好的方法,祖衝之要采用劉徽的方法去超越劉徽的結(jié)果,工作量極其巨大:要從圓內接正6邊形、12邊形、24邊形,一直算到12288邊形和24576邊形,要分別算出它們的邊長和麵積。這中間要進行係列的加(jiā)減乘除和乘(chéng)方開方運算,涉(shè)及的運算(suàn)步驟有一百多(duō)步,有效數字高達十(shí)七八位。而在當時(shí),人們還不會用紙和筆進行列式(shì)演(yǎn)算(suàn),所有這(zhè)些計算都是通過布列算籌而得以完(wán)成的。可以想像(xiàng)這在當時是需要何等的精心和超人的毅力,祖(zǔ)衝之經過艱巨的運算,終於求得了比劉(liú)徽的結果精確度更高的(de)圓周率值。他計算出圓周率的準確值介於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jiān),從(cóng)而首次把圓周率值準確推算到了小數點後(hòu)7位。他還明確指出了圓周率的上限和下限,準(zhǔn)確說明了圓周率的取值範圍,實(shí)際上確定了其(qí)結果的(de)誤差範圍。祖衝之的結果是在當(dāng)時(shí)世界數學史上最先進的成就,直到15世紀,阿(ā)拉伯數學家卡西和(hé)16世紀法國數學家F·韋達才得出更精確的圓周率(lǜ)值。祖衝之還給出了兩個用分數形式(shì)表示的圓周率近似值:約率π=22/7;密率π=355/113。密率是分子分母都在1000以內(nèi)的分數形式的圓周率最佳近似值。該數值的分(fèn)數表現(xiàn)形式直(zhí)到16世紀才被德國人V·奧托和菏蘭人A·安托尼茲重新發現,在西方(fāng)數學史上,π=355/113常被稱為(wéi)“安托尼茲率”。鑒於密率是祖衝之在世界上最先提出來(lái)的,日本著(zhe)名數學史家三上義夫(fū)曾建議(yì)把“密率”稱作“祖率”。也正因為祖(zǔ)衝(chōng)之的這些成就,人們把他尊奉為偉大的數(shù)學家。但(dàn)就他自己而言,他推算圓周率的目的是為了應(yīng)用於天文曆法、度量衡、水利工程和(hé)土木建築等的需要。特別是他(tā)用(yòng)自己推算的圓周率考校了新莽嘉(jiā)量,大大推進了精(jīng)確測量、設計度量衡標準器的工作(zuò),促進(jìn)了計量科學(xué)的發(fā)展。
祖衝之對(duì)新莽嘉(jiā)量的校驗結果,李淳風所(suǒ)撰《隋書·曆(lì)律誌》有所記載(zǎi)。
其斛銘(míng)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冪(mì)百六十二寸,深尺,積千六百二(èr)十寸,容十鬥。”祖衝之以圓率考之,此斛當徑一尺四(sì)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庣旁(páng)一分九毫有奇。劉歆庣旁少一厘四毫(háo)有奇,歆數術不(bú)精之所致也。
根(gēn)據劉歆對嘉量的設計,嘉量斛的容積可以表示為:
1斛=π(+庣旁)2×10=1620(寸3)
劉歆的庣旁為9厘5毫(0.095寸),根據這一數字,可以倒推出他使用的π值是3.1547。祖衝之以他推算的圓周率值來驗算(suàn)劉歆的設計,發現劉歆的(de)“庣旁”不夠精確,少了1厘4毫。以祖率π=3.1415926代入(rù)上式(shì),得(dé)出庣旁值為0.1098933寸,即“一分九毫有奇”,將此值與劉歆的結(jié)果“九厘五毫”相比,劉歆的庣(tiāo)旁值確實少了“一厘四毫有奇”。所以,《隋書·律曆誌》的作者李淳風指出:之所以出現這種(zhǒng)結果,是“歆數術不精之所致(zhì)也”。這(zhè)裏雖然指出的是庣旁值不精確,實質是圓周率值不(bú)精(jīng)確。在祖衝之之前,劉(liú)徽曾以他推算出的π=3.14的圓周率值計算過新(xīn)莽(mǎng)嘉量斛的(de)直徑,但未提及庣旁,而且計算也不及祖衝之精確(què)。祖衝之是曆史上第一個明確(què)指出劉歆庣旁誤差的人。
大膽革新曆法 精(jīng)確(què)測量時間
祖衝之對(duì)當時行用的曆法《元嘉曆》作了大膽的改革。他改進了傳統測定回歸年的方法,使新的曆法在(zài)回歸年長度的測定上更為(wéi)準確。過去測定回歸年長度,通(tōng)常是在預期的(de)冬至前後幾天,用立竿測影的方法,測出影子最長的那一天作為冬至,相鄰兩個冬至之間的時間長度,就是(shì)一個回歸年。這種方(fāng)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存在一些問題,而且還(hái)容易受到(dào)冬至前後氣(qì)候變化的影響,有一定誤差(chà)。祖衝之對之作了巧妙的改革,他(tā)選擇冬至前若幹天和(hé)冬至後(hòu)若幹天分別(bié)測量正午時(shí)分的影(yǐng)長,通過比較影(yǐng)長變化,運用對稱原理推算出冬至的準確時刻。他(tā)的方法是對傳統回歸年測定(dìng)方法的重大突破,有很(hěn)高的理論意義和實用價(jià)值。他運用(yòng)這一方法,測得了更(gèng)為準確的回歸年數值(以一個回歸年的日數為365.242 814 81日,以一交點月的日數為27.212 23日)。直到宋代楊忠輔所編的《統天曆》(回歸(guī)年長度為(wéi)365.2425日(rì))時止,在曆代曆法中,祖衝之的這一數值是最(zuì)好的。關(guān)於太陽係五大行星會合周期的日數,祖衝之(zhī)的測量也得到相當好的結果:水(shuǐ)星的會合周期是115.88日(rì),這和現在所測得的(de)數(shù)據完(wán)全一樣;金(jīn)星的會合周期是588.93日,與現(xiàn)在所(suǒ)測相差0.01日。這些成就在祖衝之編製的《大明曆(lì)》中都得到了反(fǎn)映。
祖衝之還把歲差概念引進了曆法。歲差現象是東晉天文學家虞喜發(fā)現的,但一直未被(bèi)用於曆法,這是(shì)曆法推算的(de)冬至點與(yǔ)實(shí)際天象之間出現越來越大偏差的(de)重要原因。祖衝之通過長期的親身實測,證實(shí)了歲差的存在,雖然他定(dìng)的歲差值(zhí)精確度不高(gāo)(45年11個月差一度,按今測,應約七十多年才差一度),但他最早把歲差引入(rù)到(dào)曆法的計算之中,從而使得曆法編製有了更科學的基礎。
祖衝之在時間測量方麵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對閏法的修改。我國古代曆法是陰陽曆(lì),需要通過安置閏月來調整朔望月(yuè)和回(huí)歸年之間的關係。傳統上人們采用19年7閏的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但這種方法並不完善,大約200多年就要(yào)多出一天,祖衝之經過反複測算,提出每391年中置144個閏月的主張(zhāng)。他的這一主張跟現代測量值比較隻差萬分(fèn)之六日(rì),即一年隻相差52秒,這是相當精密的。
祖衝之在他的這些創新的基礎上,編製完成了當時(shí)我國(guó)最先進的曆法——《大(dà)明曆》,這一年,他才36歲。宋孝武(wǔ)帝大明(míng)六年(公元462年),祖衝(chōng)之上書要求劉宋(sòng)政府頒布實行《大明曆(lì)》,但遭到當時皇帝寵(chǒng)臣戴法興(xìng)的攻(gōng)擊。戴法興責備祖衝之的曆法“誣天背(bèi)經”。懼於戴(dài)法(fǎ)興(xìng)的(de)勢力,朝中(zhōng)百官對(duì)戴的無理攻擊大多趨炎附和。祖衝之對此毫不畏懼,針鋒相對地寫了一篇辯駁的奏章,表示了(le)“願聞顯據,以核理實”,“浮辭(cí)虛貶,竊非所(suǒ)懼”的鮮明(míng)立場,並用天(tiān)文觀測的圖(tú)像和數據回答了戴法興的責問。他說,《大明曆》依據的(de)天文事實都是“有形可檢,有數可推”的,經得起(qǐ)實踐的檢驗。通(tōng)過雙(shuāng)方辯論,宋孝武帝也知道了《大明曆》的優點,決定(dìng)在大明九年(公元465年)改(gǎi)換年號時采用新(xīn)曆(lì)。但由於(yú)種種原(yuán)因,直到祖衝之去世10年後,梁天監九年(公元510年)《大明曆(lì)》才被政府正式采用(yòng),這標誌著(zhe)他的改革思想已經被人們所接受。《大(dà)明曆》在南朝境內一直沿用(yòng)到陳後主禎(zhēn)明三年(公(gōng)元(yuán)589年),前(qián)後使(shǐ)用了整(zhěng)整八十年。正是由於祖衝之在天文學上有突出貢獻,現代天文學者為了紀念他,把月球上的一座環形(xíng)山稱為(wéi)“祖衝之山”。
成功複原指南車 方位測量留佳(jiā)話
在空間方位測量(liàng)方麵,祖衝(chōng)之成功地研製(zhì)出了指南車(chē),為中國計量史留下了一(yī)段佳話。
關於指南車,古代有許多傳說,有一個傳說:最早的指南(nán)車是黃(huáng)帝發明的。黃帝的軍隊在(zài)與蚩尤作戰(zhàn)時,遇到大霧,不辨方向,無法取勝,於是黃帝便(biàn)製造出(chū)一輛指南車,利用它來(lái)識別方向,使軍隊在大霧中(zhōng)不致迷失方(fāng)向。依靠指南車的指引,黃(huáng)帝(dì)的軍隊取得了勝利,生擒了蚩尤。另一個傳說認為(wéi)指南車是周公發明的。周(zhōu)公協助武王推翻了暴虐的商紂王(wáng),建立了周朝。武王(wáng)去世(shì)後,周公又代成王(wáng)治理國家,一時(shí)天下太平,王邦來賀,就連在遙遠的南方的越棠氏也派使者前了(le)祝賀。周公為了感謝他們的盛意,就造了指(zhǐ)南車送給他們,以便他們在歸途中不至於迷(mí)失方向。
黃帝或周公(gōng)發明指(zhǐ)南車的(de)傳說,其真相如何,很難考辨。根據文獻記(jì)載,東漢時大科學家張衡製造過指南車,三國時北魏的發明家馬鈞也製造過指南車。馬鈞經過發奮鑽研,成功地製造出了(le)指南車的故事被《三國誌·魏書·方(fāng)技傳》記載了下來,從而成了中國古(gǔ)代關(guān)於指南(nán)車的最早的可信記(jì)載。
張衡和馬鈞的指南(nán)車都失傳了,但人(rén)們對指南車的關注卻熱(rè)情不減。《晉書·輿服誌》曾記載說:“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xià)製(zhì)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chē)雖回運(yùn)而手(shǒu)常南指。大駕出行,為先(xiān)啟之(zhī)乘。”劉宋王朝的奠基人是後(hòu)來被追封為武帝的劉裕(yù),劉裕當年(nián)平定關中後秦政(zhèng)權時,得(dé)到了後秦政權的一輛指南車(chē)。該車雖然具有指南(nán)車(chē)的形狀(zhuàng),但設計卻不夠精巧,以至於每當車子隨儀仗隊出行時,就(jiù)得有一個人藏在車內,依靠人的轉動使車上木人的手臂指向南方(fāng)。祖衝之對該車早有所(suǒ)知,多次提出應該對之加以改造。後來,蕭道成把持劉宋王朝朝(cháo)政,他就把改造(zào)這部車子的任務交(jiāo)給了祖衝之。祖衝(chōng)之大膽地把木構件改用銅製,經過精心推敲和反複測試(shì),成功地設計和安裝了其內部機械裝(zhuāng)置,使得該車“圓轉無(wú)窮而司方如一(yī)”,具備了自動指南的功能。當時,北方有(yǒu)個叫索馭驎(lín)的,號稱自己也能造指南車,蕭道成就讓他和祖衝之各造(zào)了一輛,公開比試。比試的(de)結果,索(suǒ)馭驎那輛指向係統的誤差很大,很不好使(shǐ),索馭驎隻好把它毀掉了。而祖衝之的指南車卻製造得非常好(hǎo),不論怎樣轉彎,木(mù)人所指示的方向始終不變,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可。祖衝之的複原被公認是馬鈞以(yǐ)來(lái)最好的。
祖衝之博學多才,精通音(yīn)律,平生著述很多,《隋書·經籍誌(zhì)》著錄有《長水校尉(wèi)祖衝之集(jí)》五十一卷,散見於各種(zhǒng)史(shǐ)籍記載的則有像《綴術》、《九章算術注》、《大明曆》、《駁戴法興奏章(zhāng)》這樣的科學(xué)作品,有像《安邊論》這樣的政論作品,有像《論語孝經釋》以及關於《易經》、《老子》、《莊子》的注釋等哲學作品,還有像小說《述異計》這樣(yàng)的文學作品。其著述內容之豐富、所涉範(fàn)圍之廣泛,由此可(kě)見(jiàn)一斑。可惜的是這些(xiē)著作絕大部(bù)分都已經失傳了。
(本文作者為上(shàng)海交(jiāo)通大學(xué)科學(xué)史與科學哲學係教授)
內容(róng)推薦
更多>2019-11-15
2019-11-05
2019-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