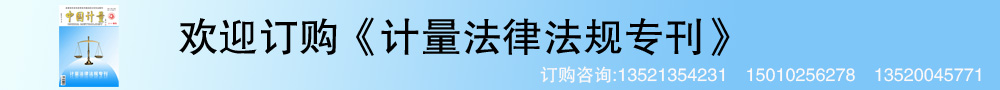
我1955年從北京機(jī)校畢業後直接分(fèn)配到原第一機械工業部計量檢定所。當時的計量(liàng)所籌建不久(jiǔ),而且(qiě)還在建設,但卻開展了不少業務工作。技術工作主要由長(zhǎng)度(計量)組和(hé)熱力(計量)組承(chéng)擔。熱力組分成熱工(計量)和力學(計量)兩個部分,力學是搞測力(lì)硬度,而熱工開展的工作基本上是溫度計量,且主要是高溫部分。無論是測力硬度還是高溫(wēn)計量都(dōu)是一機部所屬企業亟待開展(zhǎn)和加強的工作。“熱工”下麵又分為兩攤,一是(shì)(計量)監督(以下簡稱監督組),另一是(計量)檢(jiǎn)定(dìng)(以下簡稱檢定組)。我一開始就分配搞監督,這是我走出校門參加工作所接(jiē)觸的第一(yī)項技術業務。
當(dāng)時計量工作的方針概括為八個字:“準確一致 正(zhèng)確使(shǐ)用”,簡稱為計量(liàng)工作八字方針。一機部的計量工(gōng)作都貫徹這個方針,監督組當然也不例(lì)外(wài)。具體任務是調查(chá)、了解情況,發現問題,提出建議。其中了解一機部(bù)重點企業溫度計量(liàng)工作情況是主要內容,特(tè)別是在(zài)開始階段,它包括:加熱設(shè)備的名稱、型號、工藝溫度及準確度要求;計量儀器的類(lèi)別、數(shù)量及使用(yòng);機構或人員的(de)配置(包(bāo)括人員的文化水平、從事溫度計量的資曆);規章製度等(děng)。對於調查中發(fā)現的問題(tí),能解決的就(jiù)地解決,不能解決的帶回單位綜合(hé)考慮。建議的提出,屬於具體技術問(wèn)題一般(bān)向儀器管理人員和(hé)使用人員直接提出,對於諸如(rú)方針政策,機構、人員、儀器設備(bèi)的配置,經費等(děng)大的方(fāng)麵要和廠領導(dǎo)麵談(tán)。當時強調要盡可能地爭取(qǔ)技術副廠長或總工程師的接見,以引起廠裏的重視。當(dāng)時工廠乃至(zhì)整個社會對(duì)於計量認識不足、甚至知之(zhī)甚少,與廠領導麵談主要目的是宣傳計量工作的重要性,計量與生產的關係,以取得廠裏的重視和支持,當時下廠的介紹信都是從一機部開出,也有這(zhè)種考慮(表明(míng)是(shì)代表部進行監督性調查(chá))吧!監督組的人(rén)員全部是1954—1956年從一機部所屬機校畢業的學生,這(zhè)些二十出頭的小青(qīng)年和廠(chǎng)領導談話開始還真有點怵頭,不得不作一些精心準備,硬著頭(tóu)皮上陣。好在廠領(lǐng)導們工作再忙也會抽時間接(jiē)見,並以禮相(xiàng)待,認真聽取我們的意見(jiàn)和建議。根據調查結果進行匯總、研究、總結,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調研,為以後的計量工作(zuò)開展提(tí)供了第一手材料,如人員的培訓、資料的譯編以及檢定組研製二等標準鉑銠10—鉑熱電偶,請蘇聯專家協助、指(zhǐ)導工作等。
工作(zuò)的性質和任務決(jué)定了(le)工作的方式方法,監(jiān)督組的下廠時間相當多,因(yīn)此,我參加工作一年多時間兩次出差東北、一次中南、西南地區。當時一機部所屬工廠(chǎng)都在東北、華(huá)東、中南、西南,開始階段都(dōu)是兩人一組(zǔ)分(fèn)赴這幾個地區。
我第一次(cì)去東北是隨高佩珍同誌一起、由她負(fù)責。 1955年9月18日登上旅程,這時距我開始參加工作的時間僅(jǐn)有40天。因為(wéi)所學的金屬切削專業(yè)與所要搞的熱工計量相差甚遠,所以此行說是工作、實際是學習,跟老同誌學(xué)習,通過(guò)實踐學習。此次(cì)東北之行共去沈陽、撫順、哈爾濱、齊(qí)齊哈爾、長(zhǎng)春5個城(chéng)市,12個廠,其路線(xiàn)是(shì):北京(jīng)→(經沈陽)撫(fǔ)順→沈陽→哈爾濱→齊齊哈(hā)爾→(重返)哈爾濱→長春→北(běi)京。12個廠是(shì):撫順重型機器廠; 沈陽 變壓器廠、風(fēng)動工具廠;哈爾濱 電機廠(chǎng)、電池廠、工具廠、軸承廠、量具刃具廠;齊齊哈爾 機車車輛廠、第(dì)一(yī)機床廠;長春(chūn) 第一汽車製造廠(代號652)。從9月18日啟程到(dào)10月24日回(huí)京總(zǒng)計36天(tiān)。
我們所去的這些工廠大都有參加一機部計量檢定所舉辦的上海訓練班學習的學員,所以一般是先找學員,然後去他們所屬的部門。廠裏的熱工計量(liàng)不像長度計量那樣,有統(tǒng)一的專門機(jī)構負責(一般是在檢查(驗)科下設有計量室),而是由一個或多個部門代管或(huò)分管,其中有(yǒu)實驗室、化驗室、中心實(shí)驗室、檢查科(kē)、設備(bèi)科,也有少數是由以上部門與車間分管,職能部門管“檢定”;車間管儀表(biǎo)和使用。像(xiàng)當時‘652’那樣有專職部門(儀(yí)表車間)管理的隻是極個別(bié)廠。到廠以後,分管熱工(gōng)計量的部門領導會作一般的(de)介紹,主要(yào)還是學員進行全麵具體的(de)介紹,然後去車間(最主要的(de)是熱處理車間,有(yǒu)的廠還有鑄造、鑄鋼及鍛造車間,)和化驗室了解(jiě)儀器、設(shè)備(bèi)及安裝使用(yòng)等(děng)情況,這些都要作詳細記錄。在此基礎上再和部門領導談我們的一些看法和(hé)建議並征求對我單位的意見和(hé)要求(qiú)。
當時我國(guó)的熱工計(jì)量真是薄弱(ruò),存在的(de)問題和需求相(xiàng)當多,盡管我們所去(qù)的廠基本上都是蘇聯援建的重點項目。所(suǒ)用儀器設備來自多個(gè)國家,以蘇聯(lián)的為多,此外還(hái)有國產的、東德的,甚至還有(yǒu)美(měi)國(guó)的。沒有專(zhuān)門的計量管理和技術機構;缺乏標準儀器(如熱電偶(ǒu)、電位差計)和檢定用設備,隻有少數廠有從蘇(sū)聯進口的;缺少專用和修理用材料、備件(如補償導線、標準電池);儀器的安裝使用不當(如環境惡劣、熱電偶參(cān)考端溫度(dù)高且不加修正);大多沒有專門的規章製度;急需技術人員的培訓和專業知識(shí)的普及,這些都是普遍現象,亟待解決。有的提(tí)出要求進行人(rén)員培訓(xùn)、提供專業技術資料;有的提出統一解決(jué)儀器設備問題,特別是(shì)標準儀器(當時控(kòng)製嚴格,除蘇聯援建配套的以外,需要補充和增購的、都是蘇聯專家直接向一機部提出計劃)。有兩個廠提出標準電(diàn)池凍壞,652就希望我(wǒ)們向部裏反映由蘇聯進口的標準電池運輸中凍壞問題(tí)。
在每個廠工作的最後一環(huán)、也是最難的一環是向(xiàng)廠領導匯報和建議,難的原因之一是他們都很忙。相當多(duō)的廠是司局級編製,但(dàn)當時的廠長沒(méi)有豪華的辦公室,沒有高級轎車,沒有(yǒu)先進的辦公設備,在廠長辦公室映入眼簾的是的是各種圖表、錦旗、響(xiǎng)個不停的電話和進進出出、行色匆(cōng)匆的身(shēn)影。如果把工廠(chǎng)比作戰場,那麽(me)廠長辦(bàn)公室就是指揮部,廠長們就是指揮員。要想得到(dào)指揮員的接見必須預約(yuē)、而且常常(cháng)不止一次,下麵一段筆(bǐ)記(jì)可見一斑。
“下午去另外一個廠,會見的總工程師是、名字非(fēi)常熟悉的婁希翱同誌。……雖然上班了,他才吃(chī)中午飯,而且(qiě)是邊(biān)吃(chī)邊與人談話。也就(jiù)是在(zài)吃飯當中接見了我們,用不著說(這就是)為什麽我們來過3次、打過三次電話才能見麵(miàn)的原因。……”
( 1955年10月18日 於哈爾濱(bīn)市工作筆記)。
1956年夏秋(qiū)之際我和鄧錫祥同誌去(qù)中南、西南地(dì)區,跨越5個省,去了6個城市、10個廠。路線是:北京→(經武漢)長沙→湘潭(tán)→醴陵(鄧)南昌(李)→(重返)長沙→廣州→(經柳州)貴陽(yáng)→昆明→(經重慶(qìng))→北京。10個廠(chǎng)是:長沙機床廠、湘潭電機廠、湘潭電線(xiàn)廠、醴陵陶瓷廠、南昌柴油機廠、廣州造船廠、貴陽礦山機器廠、昆明機床廠、昆明電機廠、昆明電線廠。從(cóng)八月(yuè)中旬出發(fā)到十月(yuè)初返回北京總計也是一個多月。
在這兩個(gè)地(dì)區工作的內(nèi)容(róng)、方式和過程與東北基(jī)本相同,但由於地區和(hé)季節的關係,這(zhè)次出(chū)差還是比較艱苦的,不過也很有意思,特別是西南少數民族地(dì)區。我當時做(zuò)過一些筆記,可惜後(hòu)來都已遺失,下麵就所能想起的作一些回顧。
八月(yuè)中正(zhèng)是(shì)暑熱天,號稱三大火爐之一的武漢更是熱不(bú)可忍,估計溫度至少38℃,即使呆著不動也是汗流浹背(bèi)。所以從北京乘火車抵達後(hòu),不(bú)敢停留,連夜乘(chéng)慢車趕赴長沙。臨時買的站票,過道裏擠滿了人,轉(zhuǎn)身都困難,後來從一個小站下車(chē)走到臥鋪車,還算幸運、搞到兩張臥鋪票。長沙的熱比起武漢毫不(bú)遜(xùn)色,湘潭也是如此。在湘潭、住宿處室溫太高,好多人夜間都搬到(dào)室外睡,入鄉隨俗、我們也這(zhè)樣度過(guò)了幾夜。從(cóng)湘潭我和老鄧分開,他去醴陵,我去南昌,然後在長沙會合同去廣州。廣州(zhōu)沒有傳說和想象(xiàng)中那麽熱(rè),至少(shǎo)比湖南要好多了,特(tè)別是到了晚上,涼風習習,很(hěn)是爽快,且無蚊蟲之擾,這可能與所住招待所臨(lín)近江邊(biān)有關吧!廣州(zhōu)工作的結束也是中南地區工作的結(jié)束,下一步就是(shì)包括雲、貴兩省的西南地區。
從廣州(zhōu)乘輪船逆西江而上,經肇慶至(廣西)梧州,再換乘小船沿潯江、鬱江至貴縣。從貴縣乘火車至柳州,轉乘慢車至金城江,據(jù)說這條鐵路還是抗戰時期的,再往前走就隻能改乘汽車了。休息一夜乘汽車經(貴州(zhōu))都勻(yún)到達貴陽。
初識貴陽(yáng)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以至後來到這裏工(gōng)作,算是預示、也是(shì)緣分吧!所以要多寫上兩筆。貴陽是個(gè)內陸城市,雖然是西南地區的樞(shū)紐,抗戰時期的大後(hòu)方,但當時交通很不發達(dá),對外聯(lián)係隻有公路。我想可能正是所處的地理位置和相對發達的公路,使得他具有一座非常漂亮而又實用的客車站(長途汽車站),這應當是當時貴陽的標誌性建築。寬闊的停車場、舒適的候車室,特別是那黃黃綠綠(lǜ)的琉(liú)璃(lí)瓦,從很遠就可看到,真可以和北京地安門外的大屋頂相(xiàng)媲美,這不僅在當時、就是在以後相當一段時間(jiān)裏,這樣的客車站(zhàn)也非常罕見。
當時貴陽市內交通也差,隻有(yǒu)幾路公交車,我們所要去的礦山機器廠距市內隻有17華裏,也要在客(kè)車站等(děng)班車。貴陽(yáng)礦山機器廠始建於1936年,是一個(gè)大型工(gōng)程機械(xiè)裝(zhuāng)備製(zhì)造企業,也是(shì)一機部在西南地區的重點企業(yè),設備雖算不得先進(有(yǒu)的儀表還是解放前美國生產的),卻很齊全。最後的工作是汪福(fú)清總工程(chéng)師接見我們,他為人(rén)謙(qiān)和,認真聽(tīng)取了匯報、作了原則表態。說來也很有意思,三十(shí)年後我們又有機會會晤,作(zuò)為省政協副主(zhǔ)席的汪總被聘為貴州省計量與儀器專業高級職稱(chēng)評委會主任委員,我作為一(yī)般委員,所以每年都有機會見(jiàn)麵,但對於這(zhè)三十年前的往事我一直沒(méi)有提及。
告別貴陽又經過(guò)兩天旅程到(dào)達四季如春的昆明,下榻(tà)昆明機床廠招待所。昆明工作結束此次下廠任務基本完成,但‘打道回府(fǔ)’的路上還有一番跋涉。從昆明出發經(貴州)畢節、(四川)敘(xù)永、瀘州,再到重慶,一(yī)路都是乘長途汽車。汽車都是在大山中蜿蜒穿行,路麵(miàn)很窄,有時連會車都難,路況很差,時有顛簸。車(chē)子陳舊,乘客超員,過道處要加座位。每天都(dōu)是天不亮就上路,傍晚到達宿處。記得有一次趕到旅店已是深(shēn)夜,鄉村旅店照(zhào)明很差,隻(zhī)有兩盞油燈。模糊中每人抱一捆稻草,跟著有(yǒu)手電的人爬上一(yī)個木屋的頂樓(lóu)。鋪開稻草和衣倒頭便睡,好像沒好久,天沒亮又要趕路。
據錫祥回憶,在大西南的旅途中要經過一個72 拐山(據說(shuō)盤轉72次才翻過此山(shān)),當時是(shì)夏天,到山(shān)頂(dǐng)就猶如冬天一樣,又沒帶(dài)冬天衣服,隻好跟車下的小販買(mǎi)些土毛衣穿。有(yǒu)時晚上,還要打著(zhe)手電(diàn)筒(tǒng)到處去找旅館,所謂旅館隻是在地板上打個通鋪能睡覺的私人小店而已(也沒電,隻點一根臘(là))。我用小(xiǎo)書包背著(zhe)借來2000元的旅差費,白天抱在懷裏,晚(wǎn)上(shàng)當枕頭,整天提心吊膽,椐說那裏常有土匪。曆時近一個月行程千裏,最後也隻花了3百多(duō)元 錢的旅費(但(dàn)相當我一年的工資了),後來還受到財務處的批評(說借的太多了),但當時又有誰能告(gào)訴準確的預算呀?回憶過去往事,就像唐僧取經一樣,曆盡(jìn)艱難險阻,也很有趣。
就這樣曉行夜宿直(zhí)到瀘州才算告(gào)別那崇(chóng)山峻嶺,9月底到重慶,這一行程共計四天的時間。從重(chóng)慶乘船沿江而下經武漢轉乘火車(chē),一路順暢(chàng)抵京。
第二次去東北(běi)好像也是1956年,由金華彰同誌負責,張岱明、秦(qín)蔭堂和(hé)我(是否有周嘉齡已記不清)參加。此次下廠的目的除前麵提到的以(yǐ)外,還有為搞協作組作準備。由於筆記的遺失,多年的往事記憶中已經模(mó)糊。印(yìn)象深的是沈陽電線廠,這是蘇聯援建的一個新廠,熱工計量完備,機構、規章製度健全(quán),工作和標(biāo)準儀器設備都是援建(jiàn)配套而來,技術力量也較強,當時(shí)是想請他們負責在沈陽搞協作組的。據錫祥回憶,沈陽地區的協作組是由沈陽第一機(jī)床廠徐海涵任組長,沈陽風(fēng)動工具廠李月珍任副組長。
就我的印象,熱工監督(dū)工作到1957年一直在進行,協作組搞(gǎo)的時間還要(yào)長。
金華彰同誌作為監督組的(de)中堅力量搞了很(hěn)多工作,比如曾經請長度組李慎安同(tóng)誌(zhì)給熱工監督組(zǔ)做過報告,專門介紹長度計量開展監督工作的經驗。後來在上海、天津等地搞的協作組也都很有成效。
新中國(guó)成立後(hòu)我國計量工作初創的曆史,這段曆史的方方麵麵、點點滴滴,值得回(huí)顧,值得(dé)追(zhuī)記!建國初(chū)期,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對計量工作(zuò) 提(tí)出了新的要求,國家開始關注工業計量工作,從而建立一機部計量(liàng)檢定所。首先開展工業企業急需解(jiě)決的長(zhǎng)度和熱工計量工作,從生產實(shí)際需要出發(fā),開(kāi)展計量監(jiān)督、培訓計量人員、建立計量標準、開展檢定、解決生產過程中的計量技術問題等工作(zuò),這為我(wǒ)國計量工作全麵發展所需的必要準備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注:此文曾征求金華(huá)彰、鄧錫祥二同誌意見,感謝華(huá)彰的修改意見和(hé)錫祥的補充回憶。
(注:李培國是1955年參加溫(wēn)度計量工作的老同誌,後調貴州省計量科學研究院從事溫度計(jì)量科研技術工作,勤勤懇(kěn)懇幹(gàn)了一輩子(40年)計量工作,業務專研(yán),工作(zuò)認真,還有一定的文學(xué)水平,是我們老戰友中一名實(shí)幹家。)
欄目導航(háng)
內容(róng)推薦
更多>2020-10-09
2019-06-17